帕帕諾與《杜蘭朵》:重新定義普契尼的經典

Sondra Radvanovsky (Turandot), Jonas Kaufmann (Calaf), Ermonela Jaho (Liù), Michele Pertusi (Timur), Michael Spyres (Altoum), Mattia Olivieri (Ping), Gregory Bonfatti (Pang), Siyabonga Maqungo (Pong), Orchestra e Coro dell’Accademia Nazionale di Santa Cecilia, Antonio Pappano
February, March 2022
除了「茉莉花」這首歌曲,說到普契尼以中國為背景的歌劇《杜蘭朵》,你會想到什麼?我想到的是:最莫名其妙的主角個性設定。除了三個丑角般的中國大臣還有點人性邏輯可言,所有獨唱角色的個性設定根本是胡說一通,尤其是冷血的中國公主杜蘭朵。她要殺光外國王子的理由是為被外族俘虜致死的祖母報仇,問題是,年幼喪母的中國皇帝都沒吭聲,從沒見過祖母的杜蘭朵是在恨什麼?中國皇帝只會勸那些覬覦女兒美貌的王子們快回家,卻眼睜睜旁觀女兒藉亡母的名義胡搞?那些王子們的國家怎麼還沒殺過來?或者要接著上演殺光公主為王子報仇的戲碼?這一切鬧劇,只因為一個不知名王子的吻就解決了?這吻的神奇程度,堪比《青蛙王子》啊。這一切的一切,除了「劇本上這麼寫」,實在想不出任何解答。
指揮帕帕諾(Antonio Pappano)在這一套最新出版的唱片解說冊序文裡, 提到自己一直逃避指揮《杜蘭朵》,理由也是無法欣賞它的戲劇性。但是發現音樂的奧妙之後,帕帕諾終於改變想法,在六十二歲走進錄音室,和也是第一次演唱自己擔任角色的男高音約納斯‧考夫曼(Jonas Kaufmann)、女高音拉德凡諾芙斯基(Sondra Radvanovsky),在新冠肺炎疫情仍處高峰的時候,錄下這套唱片。演唱「柳兒」的女高音亞霍(Ermonela Jaho)是唯一演唱過自己角色的獨唱家,另一個讓人眼睛為之一亮的選角,則是演唱中國皇帝的男高音史派爾斯(Michael Spyres)。
二十世紀初期,有一批作曲家積極尋找擺脫傳統的音樂語言,像是巴爾托克、史特拉溫斯基、德布西等等。雖然普契尼已經有自己成熟的音樂語言,但是他也感受到作曲界急欲改變的潮流。帕帕諾稱《杜蘭朵》的音樂為「儀式的」(ceremonial),以義大利歌劇貫有的「儀式」,利用劇中大量的合唱、主角莫名衝動等劇情,藉由大量打擊樂器、加強銅管聲部,以及表現力必須與之對抗的弦樂聲部,表現出史特拉溫斯基式的管弦樂色彩。它的重點不在柳兒天真到不可思議的單戀,或是杜蘭朵與王子的愛情是如何開始萌芽,而是普契尼大膽加入的新聲音。
不過,它畢竟還是一部歌劇。一般相信,讓普契尼停筆在柳兒的送葬音樂,遲遲無法寫完劇尾二重唱的原因是,他不知道如何以音樂解釋在柳兒悲傷的殉情之後,可以立刻合理轉到杜蘭朵與王子炙熱燃燒的甜蜜愛情。再怎麼看,兩人的愛情養份都是來自柳兒的屍體。於是,普契尼在逝世前只留下劇尾二重唱的草稿,交代學生阿法諾(Franco Alfano)幫他完成。
《杜蘭朵》在普契尼逝世五個月後首演。流傳最廣的一則故事是:指揮托斯卡尼尼在柳兒送葬音樂結束後放下指揮棒,宣布歌劇結束,因為「大師已逝世」,第二場才演出阿法諾續完的結尾。事實上,托斯卡尼尼對阿法諾的版本並不滿意,他動手刪掉一百四十小節左右,也就是現在一般演出的版本。雖然阿法諾也沒能解決困住普契尼的問題,但是帕帕諾認為,多了這一百多小節,延長杜蘭朵與王子的爭執,在戲劇上反而比一個突兀到根本是性騷擾的吻更具說服力,因此他在這裡還原被刪去的段落(請繼續聽接下來的幾軌)。
我最喜愛這套唱片的一點,就是哪怕是一點小小的變化,樂團與歌手的呼吸、色彩都是緊緊貼合。先不論處處可聞的巧妙音色處理,經過帕帕諾「史特拉溫斯基化」後,許多大場景的節奏性與色彩確實讓人耳目一新。不提已經成為世界名曲的「公主徹夜未眠」(Nessun dorma),約納斯‧考夫曼在「柳兒,別哭」(Non piangere, Liù!)前段細膩溫柔的歌聲加上帕帕諾絕美的弦樂「助攻」與呼吸,讓人很願意相信他是一個憑笑容就能讓柳兒死心塌地的王子。亞霍有如天使的柳兒與拉德凡諾芙斯基在出場曲「在這宮殿裡」(In questa reggia)裡的幅度變化, 都是唱片中讓人印象深刻的段落。
最後,有興趣的人不妨看看這段附有錄音實況的影片,由合唱團演唱的「在東方的山上」(Là, sui monti dell'est)。在這樣的社交距離之下還能合唱,真讓人不得不佩服呀。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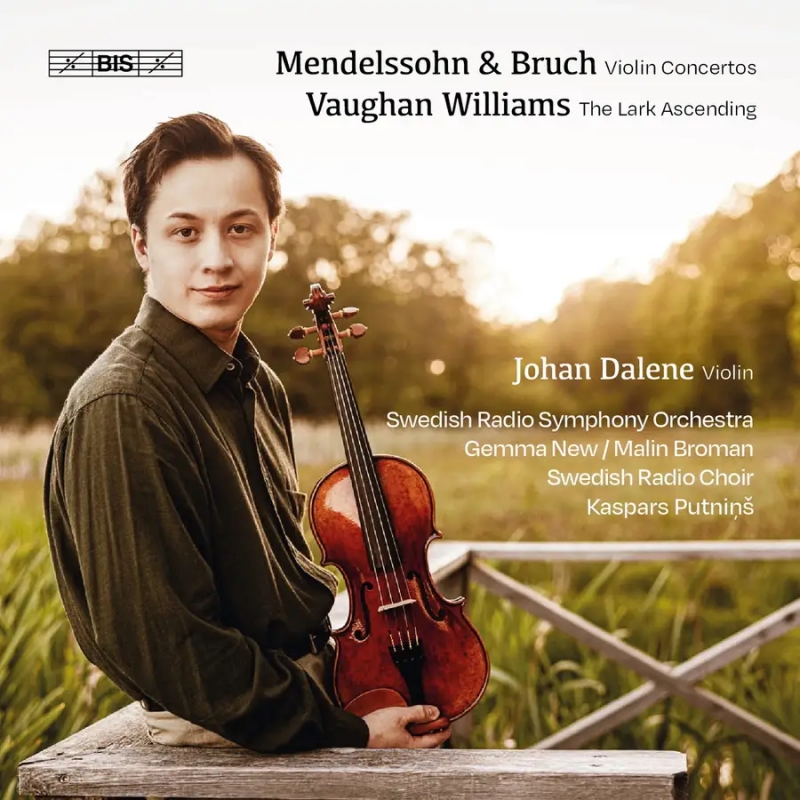


發表留言